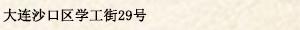故事结婚近十年,我和丈夫早没感情,他车祸
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,如有雷同实属巧合。
1
那句话是在厕所门口说的。
当时苏小小从厕所出来,那位好心的阿姨本来早解决完了,一直站在厕所外边的过道里等着她,阿姨牵着她的手,说了几句闲话,忽然就附在她耳边,悄悄说,“你最好和卓丽倩那个人保持距离。”
阿姨走了,小小瞅着她的背影,脑袋里像按了台鼓风机,嗡嗡地响起来。等她再走进办公室时,心里不免一惊一乍的。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,她和卓丽倩都是才入驻的新主,不过卓丽倩是从别的部门调入的老职工,唯有她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嫩雏儿。
说实话,和三个女人同处一个屋顶下,即使没有别人的警告,她也有些发憷,三个女人一台戏,这四个女人天天腻在一块,不出点事才怪呢!何况还有漂亮的卓丽倩,这个人们眼中的是非女人,结婚两个多月就离了婚,关于她的传闻满天飞。
一周后,孙秀珍嚷着要做东给两个新来的妹妹接风洗尘。她年龄最长,自诩为大姐。郝文笑着说算她一份吧,两个老人请两个新人。孙秀珍却坚持这次她请客,“不行,我是大姐,这次一定我请客,大家凑在一块是缘分,少不了要经常在一起聚餐的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吃饭时,四个女人亲昵地团坐在桌子四周,相互敬酒,其乐融融。苏小小端详着几张盈盈的笑脸,特别多看了几眼卓丽倩,卓丽倩的一双笑眸闪闪发亮,像个孩子似地大笑。苏小小内心突然一动,她有些埋怨那个要她提防卓丽倩的阿姨了。
转瞬间,春寒料峭的日子溜走了,河水潺潺,春暖花开。苏小小望着窗外烟雨蒙蒙的绿意,嗅着飘进来的浓酽的春天的味道,感到这个新办公室对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好来处。
当然,怎么说呢,也并不总是一切天下太平。因为这是四个女人啊,并且是各怀心事的四个女人!女人,女人,好像天生就是心眼比针鼻还小,天生就要窝里斗。
原来这间办公室里只有孙秀珍和郝文。一山容不下二虎,如果想风平浪静,必须一方压倒另一方,或者一方甘心臣服另一方。这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,甚至铁哥们姐们,也很难逃开这种规则。
孙秀珍和郝文之间,当然也遵循这种规则。在三十多平米的空间里,孙秀珍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权威感。孙秀珍喜欢唠叨,郝文就当一个听众,或许这听众不那么忠诚,有时不免敷衍,但这丝毫不妨碍大局和谐。
现在,两个新主来了。苏小小是本分的女孩子,懂得眉眼高低,而卓丽倩就不同了,是一个喜欢发飙的主儿。原来的格局被悄然打破。
孙秀珍特别喜欢谈她的老公,兴奋时如打了鸡血一般,话语就像厕所里坏了阀门的自来水,能把办公室的桌椅飘起来,从她老公的工作,到她老公早晨顺便熬的小米粥,偶尔收拾的一条鱼,她都会眉飞色舞地谈半天。老公是女人的另一张脸,孙秀珍自己这张脸实在是没什么可讲的,便卯足了劲谈自己的老公。
孙秀珍经常从家里拿一些五花八门的吃食,殷勤地分给每个人。她会把东西一直塞到你的嘴里,看着你咽下去才作罢。她还会总是强调,你大哥出发带回来的,又去外边考察了一周。于是,办公室的其他人吃着新疆的葡萄干,天津的大麻花,西安的大石榴,洛阳的猕猴桃,喝着海南的椰子汁时,也都知道了孙秀珍的老公曾到哪里出差。
孙秀珍说起自己的老公时,很注意观察其他三个人的神情。对面的郝文不时抬头笑一笑,插科打诨一句,苏小小也会偶尔与孙秀珍交流一下目光,表示自己在听她的话,唯独苏小小对桌的卓丽倩,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,盯着手机,窝在那里一声不吭。
孙秀珍睨一眼卓丽倩,大声和她说话,不知卓丽倩听见与否,反正她依然盯着手机,一句也不接茬。
孙秀珍的脸就挂不住了,沉下脸。
郝文一旁打圆场,“卓丽倩戴着耳机呢,没听见吧?”
苏小小也赶忙小声附和着,“是啊,是啊,她戴耳机呢!”她瞄瞄卓丽倩,卓丽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但她明白,卓丽倩不过是装傻罢了。
卓丽倩属于天生的婴儿肥,是那种丝毫不影响她的姿容,却平添几分风韵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,她时常嚷着胸口憋闷,所以只要进了办公室,就一阵稀里哗啦地把窗子全部打开。
孙秀珍的桌子就在窗下,据说她的眼睛有迎风流泪的毛病,所以原来是否开窗子由她决定。
如今,卓丽倩甚至不看她一眼,推开窗子就走。她常常刚一离开,孙秀珍就灰着脸站起来,啪的一声关上窗子。那边卓丽倩却静寂无声,她又盯着手机,全身心投入到网上购物或游戏中去了。
但有时孙秀珍偶然出去一趟,回来窗子又大开了。她乜斜一眼塞着耳机的卓丽倩,气哼哼坐下来,好长时间一声不吭。而卓丽倩愣像没事人一般,该干什么还干什么,嘴里还偶尔飘出半句小调。
六月份以后,天渐渐热起来。这间办公室原本是没有空调的,现在人多了,领导就给安装了空调。但问题也随之来了。孙秀珍怕冷,不能吹空调,而卓丽倩怕热,有空调依赖症。只要有机会,卓丽倩就把空调遥控器握在自己手里,想开就开,想关就关。
孙秀珍罩着厚厚的运动衫,一只手托着腮盯着电脑,但她的鼻息是粗的,咻咻喘着气。
空调的遥控器突然不见了,卓丽倩烦躁地在屋子转来转去。而孙秀珍坐在那里纹丝不动,脸上的皮肤都漾着得意。
翌日刚上班,孙秀珍就哇哇大叫,说抽屉上的锁被人撬了,苏小小和郝文问丢东西了吗,孙秀珍支支吾吾说没有。
然后卓丽倩来了,从粉红色的背包里拿出一样东西,对着空调一晃,又迅速把东西塞回包里,霎时,空调蜂鸣起来。孙秀珍的脸红一阵白一阵,一团蓝色的火苗在她眼眸里幽幽燃烧。
不知从哪一天起,不知从何时起,孙秀珍和卓丽倩两个人已经针尖对麦芒,有了点水火不相容的劲头。而苏小小和郝文则一副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的淡然模样。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
一天上午,卓丽倩又没有来上班,她想不来就不来。孙秀珍冲着卓丽倩的空座位一努嘴,对苏小小坏笑几声,“你看卓丽倩早晨又起不了床吧,她单身还能闲着?”
苏小小瞥了一眼郝文,郝文也正瞅着她,眼神期待下文,苏小小期期艾艾地说,“她,她倒是开玩笑说她找了N个男朋友了!”
“不知祸害了多少男人!”孙秀珍有些义愤填膺地用食指点着卓丽倩的桌子和椅子,好像那桌子椅子也沾了很大罪过。
郝文只是淡淡的未置可否的笑笑,然后就埋头做自己的事了。苏小小在郝文转头的刹那间,却从她的眼底深处捕捉到了一丝怅惘之情。
2
不知是什么原因,还没有等到天大热起来,一个多月以后,卓丽倩竟然调去了另一个新岗位,离开了这间办公室。
那是一个轻松的闲差,一周不来上班,都不会有人注意,正好适合卓丽倩的散漫性子。办公室里倒是清静了,再也没有人和孙秀珍较劲,孙秀珍的气色好多了,又恢复了过往的神气活现。
不过,孙秀珍心里好像挺惦记卓丽倩这个人,时常会突然蹦出一句,卓丽倩找对象了吗,还不打算结婚吗。苏小小只说不知道,搪塞过去罢了。
“你会不知道,你们不是朋友吗,替她保密啊?”孙秀珍盯着苏小小几秒钟,充满揶揄的意味。
苏小小不吭声了。她心里滚过酸涩的味道,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她在想,这世间有真正的朋友吗?她和卓丽倩算是朋友吗?
半年前,她大学毕业刚来到这个单位,两眼一抹黑,感觉自己像一颗油珠掉进了水中,无论怎么努力,都不能与水相融。渐渐的,她品出点味儿来了,人们是欺生的,欺负她这个新人!
但她被欺生的原因还有一层,她是农村来的,在这个小城市,她孑然一身,无有任何权贵可以攀附,人们的嗅觉是如此灵敏,很快就嗅出了在她还算俊俏的外表下面,是一副柴禾妞的土胚子。
苏小小也明白在一个环境中,必须要有一个好朋友,以便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无原则地支持自己,可以避免被孤单。
她想在同室的三个人中,寻找一个朋友。她还是首先选择了卓丽倩。虽然已经被警告过远离卓丽倩,但一抬头就看见这张笑起来十分妩媚的脸蛋,竟也生出一些耳鬓厮磨的好感。
其实还有一个原因。卓丽倩敢和孙秀珍较劲,这说明了什么呢?郝文不敢,对孙秀珍一副逆来顺受的恭敬模样。苏小小自己更不敢,她是弱势中的弱势,没有根基,一旦招惹出什么麻烦,会立刻被穿上小鞋,所以她处处一副与世无争的乖巧样子。唯独卓丽倩,任性的那么赤裸,这一点对苏小小很有吸引力!
孙秀珍是霸道的,但她婉约隐晦,俗不可耐中有几分家常菜的味道,而卓丽倩却挟风带棒,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。苏小小对这样一个人充满迷惑,进而有些着迷了。
卑俗也罢,心机也罢,孤独也罢,苏小小就很主动地向卓丽倩示好了,虽无趋奉之意,喜欢之情却表达的恰到好处。人是那么的热爱虚荣,喜欢被捧着的感觉,女人之间亦如此。你来我往几番之后,苏小小和卓丽倩已经很熟稔了,几乎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当然,苏小小主要是卓丽倩的倾听者,她也很乐意这个角色,她喜欢听,且不由自主的因势利导,而卓丽倩亦步亦趋,如数家珍讲述自己和众多男人之间的故事。苏小小惊叹之余,不免遗憾她注定是与这类故事无缘的。
卓丽倩是怎样一个人呢?她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女王,而她的臣民则是周围的男人,好像只限于男人,女人都对她不那么友好,而她对女人也有某种骨子里的反感,当然除去她的母亲。
她倒没有太在意,依然天马行空,我行我素,这起码说明她是一个正常人,不会陷入同性恋的泥沼。记得从初中开始,她的身边就围满了男孩,然后长大了,到处都会有男人宠着她。
她和一般的漂亮女孩不同,她不拒人于千里之外,冷冰冰地孤芳自赏。恰恰相反,她喜欢与那些想亲近她的男人,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,然后玩玩感情游戏,品尝心动间或心痛的滋味。她的感情之路就像狗熊掰棒子,掰一个丢一个,掰一路,丢一路,所以,她至今没有找到她的真爱。
其实,她也向往永恒的爱情,但真爱总是那么遥不可及,有时她以为找到了,全身心的投入,但转瞬即逝,就像她的婚姻,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,她就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掉了,因为婚后不久她对前夫的热情竟然一落千丈。
她曾经严肃地审视过自己,难道她是天生的喜新厌旧型,后来她更坚信自己是纯粹的爱情至上者,她的真爱还没有出现,她依然在寻觅的路上。
难道不是吗?她的内心明明燃烧着爱情的渴望,更会为电影中的爱情唏嘘不已,哭的一塌糊涂。不过有时,她也恨那些匍匐脚下的男人,怎么就那样经不起推敲呢?在她面前,站都站不起来,让她一次次对爱失望。
近两年,自从她离婚单身以后,男人们就更加应接不暇地涌到身边。有单身男人,更多的却是已婚男人。
她经历了婚姻,比原来成熟了,应付各种男人可谓驾轻就熟,游刃有余。她很衷情这样的生活,充满浪漫而新奇的情趣,所以,她一次次和男人们踏上爱情之旅。
至今,她在男人那里还没有失败过,这使她愈加自傲,同时对男人亦愈失望。失望的另一面是渴望,她心中看不起男人,认定所有男人都逃不掉色的诱惑,但冥冥中又相信那个不一样的男人在远方迄待她的发现,所以她与男人们的故事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,今生今夕不知是何年?
而与别的女人,她的同类,则几乎是完全疏离的。勿须讳言,在女人们嘴里,她有不好的声名,女人们把她看做了害群之马,也很少有哪个大度的女人愿意走近她,和她成为朋友,而她竟没心没肺地不在乎这些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,她谨记鲁迅这句话。而别人说她是破罐子破摔,死猪不怕开水烫。
但,怎么说呢,不知何时,她却无端有了失眠的毛病,脾气愈来愈暴躁,反复无常,夜里,她常常大睁着眼睛,临近天亮,才朦胧睡去。她竟渴望有一个人能陪她说点什么,但这个人不能是她身边的男人,因为她对身边的男人向来矜持。
然后,苏小小走到了她的面前。之前,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小鸟依人地顺从于她,她有一种崭新的感觉,与那些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截然不同。
自从她进了这个办公室,很快就和孙秀珍顶了牛,成了冤家对头,因为她还没有学会忍让,她习惯的是主宰别人,别人顺从她,当然别人常常都是男人。郝文躲得远远的,她亦并不在乎,本来她和别的女人就不搭界。但苏小小像一片云飘过来了,化成春雨,洒落她的头上。她和苏小小在一起,透心的舒爽,连骨头都是软的,像泡在温热的浴缸中。
苏小小总是含笑地静静地坐在对面,静静地听她说话,偶尔讶异地瞪大眼睛,却从不对她的言辞表示任何恶感,更不会与她争执什么,在她面前,苏小小是一只可爱恭顺的沉默羔羊。
于是,她完全甩脱了戒备的盔甲,她说啊,说啊,不知是苏小小无邪的眼神鼓励了她,还是她邪恶的虚荣心作祟,反正她几乎毫无保留地兜售了一切情事,从婚前的N个男朋友,到与前夫的纠葛,再到离婚后的几桩重要的情感风波,她都嘻嘻哈哈地说了。看着苏小小迷茫而略显无知的眼神,她突然觉得苏小小有点可怜,这种感觉让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。
苏小小很愿意听卓丽倩的故事。
她为什么不喜欢听呢?这说明卓丽倩信任她,再说卓丽倩的故事比电视连续剧更精彩,原来生活真的比电视剧更富传奇性。她喜欢听,她感觉面前打开了一扇奇谲的风景之门,而原来这些都在她的视觉盲点里。她吃惊,然后震惊,一桩桩情事,过眼云烟,从卓丽倩的嘴里不断吐出来,就像她用吸管轻轻吹出来的五彩斑斓的肥皂泡,美丽却虚无。她知道自己的心骗不了自己,有那么一点羡慕嫉妒恨!
她从不怀疑自己是一个纯正的人,有正确评判是非的一套体系,但她还是感觉自己滑向了低俗,因为她有种很卑微的情绪。难道就因为她的长相没有跃出大众层面,那千回百转的爱情才对她避而不现吗?那爱情又是什么东西呢?
苏小小不愿承认,她一直就是个悲催的单恋者。单恋很美丽也很杯具,单恋永远最感人,因为单恋者是一支没赶上花期的花,半途中自生自灭,香消玉损。高中时,她喜欢一个男生,经常偷偷地回头看一眼他,她还匿名给这个男生寄过明信片,可那个男生一点回应都没有。
高中毕业以后,她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,那个男生早就看上了班里一位漂亮的女同学。读了大学,同学们都忙着谈恋爱,比她丑的女生也有男生追,可就是从来没有人追过她。大三时,她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帅气的辅导员,见了辅导员就脸红心跳,她还做过一件顶傻的事情,打听到了辅导员的生日,悄悄给他寄了生日礼物。可她大学还没有毕业,这位辅导员就结了婚。而直到她大学毕业,辅导员也叫不上她的名字。
所以,当卓丽倩问她找过几个男朋友时,她沉吟半晌,说只谈过一次,如果说一次也没谈,未免太惨了。当卓丽倩笑嘻嘻地追问她有没有经验时,她的脸颊一阵滚烫,认真地摇了摇头,还发起了誓,逗得卓丽倩哈哈大笑。
彼时,她深信她和卓丽倩之间还是建立了一些友情的。友情是什么呢,有人批驳现代友情充溢社会性和功利化,但为了被孤独算不算功利呢?其实,人活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功利,养儿防老,饮水思源,亘古不变。
3
苏小小是在一爿小吃店里遇到郝文的。她经常来这儿吃拉面,三元钱一碗,吃了面再喝汤,可以把肚子喂得饱饱的。她走进小店,逡巡四周,想寻找一个好座位,一眼就望见了郝文。郝文坐在那里很显眼。她和郝文的眼光相遇了,径直朝她走过去。
她刚一坐下,郝文就淡淡地向她介绍,“这是我对象。”
她这才注意到郝文身边的男人。她原来以为他是小店的顾客。他冲她非常友善地笑了笑,但在他友善的微笑里,她却读到了一个男人的怯懦。
他坐在那里,显得无精打采,像一堆满是皱褶的衣服,和郝文无有一点夫妻相,怎么看都是别扭的。郝文虽然算不上漂亮,但却如空谷幽兰,弥发着淡淡的馨香。苏小小突然心中一颤,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。是的,她在办公室从没有听郝文说起过自己的家庭,好像郝文是福利院长大的孤儿。想到孙秀珍在办公室那种空穴来风的优越感,倨傲而世俗的面容,苏小小心中一阵抽搐,忽然明白她和郝文其实才是真正的同路人!
郝文身上好像天生有一种冷冷的伤感的东西,阻拒人于几步之外。她总是淡淡的,淡淡地笑,淡淡地说话,和她呆在一起几个月了,苏小小就没听见她畅亮地笑过,即便孙秀珍和卓丽倩之间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较劲,郝文也只是淡淡的模样。她感觉郝文这个人不好接近,所以就那么不咸不淡地处着。
今天,她和郝文面对面坐着,吃着各自碗里的拉面,说着不着边际的一两句闲话,感觉好极了。多么轻松惬意,这是她和卓丽倩在一起从没有的感觉。和卓丽倩在一起,她紧张,有一种被追赶的感觉,虽然她对卓丽倩一直微笑,但微笑下面却是剥皮见骨的伪装。
“找对象了吗?”
“还没有。”
苏小小笑笑,不知为何,她瞅了一眼郝文的老公。他一直默默吃自己的面,并不参与她和郝文之间的谈话,有时看一眼郝文,有时对苏小小笑笑。
“女孩子找对象可不能马虎,要沉下心,找一个喜欢的人生活一辈子,不是一件容易事。”
郝文笑笑,突然问起了卓丽倩,“卓丽倩不和我们一个部门了,你和她还有联系吗?”
“哦,偶然凑一处罢了。她有时会找我陪陪她。”
“她这个人虽然名声不太好,其实也蛮不简单。”
郝文一脸认真,停顿了一会儿,“其实,并不是人人都能像她那样的,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这时,郝文的对象吃完了,从兜里掏出卫生纸,擤起了鼻涕,那种声音让苏小小咽到喉咙的饭差点吐出来,她强忍着吞下去。她注意到郝文皱起了眉头,放下了筷子。
当郝文和老公走出小店时,苏小小猛然发现了郝文的老公走路有些不平衡,他的左腿好像有点跛。望着郝文轻盈的身影愈走愈远,苏小小突然对郝文充满了同情,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啊,她会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?她必定是不幸福的。
苏小小猜对了。
其实郝文刚踏进家门,就对着老公大声喊起来,“你到底怎么回事啊?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不要当着外人那样,擤鼻涕呀什么的,人家会很讨厌的,懂不懂啊,真拿你没办法!”
然后,她走进自己的卧室,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很快,屋里传来了沉闷的哭声,应该是头上捂了厚厚的被子。
这就是郝文的生活,这才是真实的郝文。外人眼里的郝文淡淡的,安静顺从的模样,那不过是一副美好的假象,而当回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,她就扒下那一套中规中矩的铠甲,袒露出真实的自己。真实的她就是眼前这幅德性,甚至是乖张暴戾的,想吼就吼,想哭就哭。
有时在只有自己的空荡荡的家里,当孤独感排山倒海地袭来时,泪腺就成为唯一的释放通道,她的眼泪会流淌不歇,洇湿双颊,湿透枕巾枕头,眼睛红肿成一道细缝,哭完了,心里就舒服了,然后用浸了凉水的湿毛巾冷敷。
明天还要上班,一切还要继续,只要走出了这个家门,她的脸就戴上了一副面具,那上面画了一张满脸堆笑的笑脸。她是一个双面人,不知何时,她竟成了一个双面人。
在喧嚣纷乱的世界里,她违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,对所有人笑,以笑来赚取别人的廉价情谊。但她渴盼的情谊究竟在哪里,她找不到,好像别人都和她隔得远远的,而她也永远走不进别人的内心,她想根本是别人的心拒绝接受她。可她还是逢人就笑,笑得肌肉麻木了,脸上过早生出皱纹。
苏小小和卓丽倩来了,本来只有她和孙秀珍的屋子热闹起来。苏小小对她礼貌有加,亲热不足,而卓丽倩的任性使她目瞪口呆之余,只想敬而远之。但她心中也有一种隐秘的平衡,毕竟这个人可以让孙秀珍头痛了。而卓丽倩却惊鸿一现,很快又调去其他部门了。她对卓丽倩的感情是复杂的,想起卓丽倩,她的心不知为何会隐隐作痛。
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,无须讳言,郝文对生活是消极的。近一段时间,她愈来愈被一种恶劣的情绪缠绕,深重的孤独感雾霾一般把她湮没,恍惚中,她好像对生活彻底缴械投降了。她甚至羡慕那些有勇气自杀的人,但她没有勇气割破自己的动脉,只在手腕上留下几道浅浅的伤痕。
她谨记一句话,人要夹着尾巴做人。但这句话应该是警告那些尾巴翘起来的人,而她早已经主动把尾巴阉割了。自从她从乡镇中学来到城里,一切都变了。她是怎么来到城里的,好像很遥远了,足足有六年了,怎么一晃就过了六年啊!当初那是一件多么轰动而荣光的事情。她是那样年轻,才情出众,因为教学成绩出色,被市里的一所高中破格录用,可惜只有一年。
她稀里糊涂地就到了一个水利学校,以前她压根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所奇怪的学校,没有学生却有八九十位教师,没有课上,照常发工资,评职称。在这样一个学校,人员芜杂,一切都是反常的。而她除了会上课,别的一窍不通。
她是一个靠单纯智商吃饭的人,而在这个需要综合情商极高的地方,她举步维艰,很快就被边缘化了。而她有一点更显弱势,她的老公是下岗职工,不能给她丝毫庇护。
她原来不知道一个有地位的老公竟如此重要。自从她和孙秀珍一个办公室,她才明白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可以凭着老公尊贵起来,而她却处处被孙秀珍挤兑,虽是一些女人的无聊伎俩,却让骨子里心高气傲的她情何以堪?她也曾试过还击,但结果更糟。
虽然人心都有向善的愿望,但人们却是如此现实,懂得分寸,懂得关键时刻该倾向谁。她并不怪别人,如果是她,也会那样吧。
所以,郝文不得不接受现实。既然不能改变环境,就要改变自己,于是郝文试图改变自己。但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,而郝文就有了两副面孔。
郝文曾求过孙秀珍帮过一次忙。郝文的对象出了车祸,上班路上,被一辆汽车撞了。医院里,肇事者交了一些钱后,再不见踪迹。孙秀珍的老公很有人脉,但她对郝文表示了问候之后,却没有再说别的。郝文望着她高高扬起的下巴,知道她在等着她说求她的话,但郝文没有说。她去了交通事故科,在挤满人的房间里,她终于等到那位警官和她说话。
警官板着面孔,“你不要想多赖钱,双方都有责任,人家也是受害者,我这里就是要主持公正,有的人想凭一次事故吃一辈子,我不会允许。”
她听到这些话就傻了。走出事故科,她接连打了几个可以打的电话,都说没有办法。她也知道是这个结果,都是和她一样的社会边缘人,能有啥办法呢!她被逼地走投无路,晚上买了礼品就去了孙秀珍家,她没有把握孙秀珍是否会帮她。她明白,帮忙是要看身份的,要在身份的天平上称一称,有身份的人互相帮忙,而她和孙秀珍的身份相差太大。但她又必须来求她,即使人家冷脸拒绝。
两天后,孙秀珍回复她,她老公尽了最大努力,但那边很有关系。
案子结了。虽然得了一些赔赏,但郝文老公的腿却留下了后遗症。有一次,孙秀珍见了,咬着她的耳朵说,“你可不能抛弃人家哦,人家现在也算是残疾人了,你抛弃他不太好!”
这句话正戳到了郝文的痛处。她相信孙秀珍是幸灾乐祸的,她心里恨死了孙秀珍。
| |